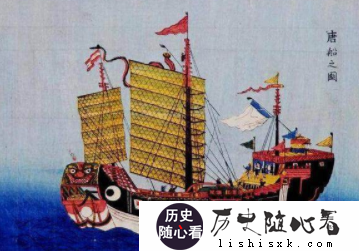任何朝代都应有“官话”,唐朝官话,大概是现在什么地方的方言?
2020-08-28 04:25:18 历史 历史 °c 繁体
A + A -摘要:唐代的官方语言在中文互联网尚无定论,争论颇多。其中主要以洛阳方言、长安话、吴语也就是南朝通语和唐朝没有统一官方语言,只有推崇的“正音”这四个观点为主。本文通过追溯中古汉语语言的发展,对《切韵》、其增本《唐韵》和与敦煌汉藏语言对比考据和推论,以举例论证比较的方法试图对唐朝的官方语言进行推理和论证,以证明唐朝的官话为长安地方方言。
唐朝作为继隋之后的又一大一统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名誉远播,与亚欧国家往来频繁。文化上无比灿烂接纳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们前来交流学习,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等特点,并且在诗、书、画、乐等方面涌现出大量名家。作为一个历史上影响如此深远的王朝,其官方语言在中文互联网上却没有明确的定论。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就像现代汉语一样,古代汉语也分成许多方言。颜之推在7世纪初曾感慨“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随即谈到了北方话和南方话的对立,而与他同时代的陆法言则更为确切地指出了“河北”与“江东”言语的区别;他们两人都点明了汉代故都长安话、洛阳话和吴国故都建康话之间的歧异。这几个方言的细分当中大多数在我们看来恐怕不过是水月镜花,其中只有其中的两支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认识,一种是吴方言,有朝鲜译音和日译吴音为我们保存了其不同时代的面貌:朝鲜译音差不多是公元5世纪的,而日译吴音则是6世纪末的,
另一种就是长安地区(今陕西西安府)的方言,关于这个方言学界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而《唐代长安方言考》一书的研究对象正是后者,此书的考释范围对这个地方方言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也就是隋唐大一统帝国(586--906)京城所在地区的宫廷和官府所说的方言进行了讨论,为我们的论点进行了其中一个维度的论证。另一个方面,敦煌出土的包含各个领域内容的古藏文文书以及两篇出自敦煌千佛洞的吐蕃人占据陇右时期(公元763年-851年)用藏文书写的藏汉对照词语残卷,也为我们从另一个维度证明了唐朝(618年—907)年间的长安地方方言为唐朝官话这一论点提供了论证;最后,由隋代陆法言所著韵书《切韵》以及孙愐私人著述命名带有官方的性质的增本《唐韵》的唐写本残卷为切入点,引其二文本内容进行第三个维度的论证。
由此翼希实现论证推论唐朝的官方语言为长安方言的这个结论。 论证唐朝官话——长安方言
要对唐朝的官话进行论证,我认为首先要假定官话的范畴,给予所谓官话一个准确的定义。究竟是作为一个绝大多数唐王朝和其文化辐射范围的人民所共同讲述的一种语言,还是作为一个供唐王朝都城百姓及文人雅士所用以沟通和辨明彼此身份的一种语言工具?如果是前者,那么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没有论证的必要了,根据多篇文献引证,唐代的各区域所讲述的语言各不相同,南北差异、东西差异极大。依照不同作者对于雅言的研究,一个共同的共识普遍的认为“雅言”或者说是共同语,在秦以后到明清之前,很长时间里头语言与文字是高度分离,也即阐明了对于试图论证唐王朝拥有这一个共同讲述的语言的不可行性。
那么如果是要论证后者呢?本文定义的官话,指的是供唐王朝的中上层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群体所用以沟通和辨明彼此身份的一种语言工具,其类似于英国中世界的拉丁文或者法语,除开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沟通、交换信息的这一功能以外,还具备了辨明彼此身份阶级的一种身份工具,即只有能正确的使用这一语言的人,才能被阶层和群体认可。因此,参考《切韵》残本及其增本和敦煌出土的文献,便是源自于此。
2.1 以《切韵》残本为例证的可行性分析
虽然说在现今的学术界,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认为陆法言主编的《切韵》一书是南京地区长江下游方言的佐证,但是这个说法其实并不算是准确的。所有的证据都倾向于说这部字典是依照北方方言编成的,最有可能是依照长安话编成的。《切韵》的编者们自己宣称,他们是以自己的方音为基础来编写这部书的,但他们偶尔也注意寻找一些别的语音,以求在建立字典编者们理想中的“正音”时有所决定。颜之推宣称错误的发音应该纠正,于是“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前代另有一些质量低劣的字典”,据他说:李仁祖、李蔚的著作少为切正,李季节《音韵》时有错失,杨休之《切韵》殊为疏野,此外被提及的还有吕静、夏侯该、周思言等人的字典,其间各有乖互,总体面貌是“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陆法言及其同好们编书的目的正是为了订正前人韵书和言语中的全部错误。不过,没有必要把前人韵书所犯的错误看得过于重要:经史注疏中保存的大量古代反切(3至5世纪)和《切韵》的反切如出一辙。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工作毕竟从修订这些古代韵书开始了:他们通过讨论,在他们提供的错综复杂的资料中决定哪个反切比较正确,再根据他们自己的读音来做出取舍。这样,为了建立一套编者们公认正确的读音,尽管当某个古音符合他们为后代变音“刊谬”的希望时他们也经常依赖古书,但编纂者白己的读音仍然被用作最终的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编纂者们的方言显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们中大多数人供职和出生的地点全都表明他们说的是北方方言。字典的首要编纂人陆法言生于洛阳。他的八位同好有六人的出生地可以考知,其中只有两人生于南方,一个是安徽人刘臻,另一个是江苏人萧该,而另外四个都是北方人:颜之推是山东人,卢思道是直隶人,辛德源是甘肃人,薛道衡是山西人。另外,隋朝的都城是长安,这里也正是他们供职的地方。
同时,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然则自史实言之,《切韵》所悬之标准音,乃东晋南渡之前,洛阳京畿旧音之系统, 而非杨隋开皇、仁寿之长安都城行用之方言。”(《从史实论切韵》)陈先生明确指出,隋统一后,陆法言 据颜之推等人的讨论写出的《切韵》乃是以洛阳皇室旧音为基础。任何时代的语言都是不同层次的叠加体,在保留了上个时代语言特征的基础上发生了一些创新现象。唐五代的语言也是这样的,它是在隋代《切韵》系语音特征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创新,但它的基础方音仍然是和《切 韵》系方音一脉相承的。[1]
而黄笑山先生认为,隋唐虽然定都长安,但是长安附 近为周、秦故地,在定都之初,长安久为僻地,标准语 并没有因首都的变更而立即改变其方言基础,因此,初唐时期的标准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切韵》时代的传 统音。到了盛唐,随着大唐的昌盛,首都长安的向心力逐渐增强,长安话逐渐取得了优势,最终在中唐前后完全取代了原来标准音的地位。(《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2]
因此,根据对于编篡《切韵》一书的几位编者的研究和两位大家观点的佐证,可以得出使用《切韵》残本与其增本作为研究比较对象和论证例证对象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2.2 以《切韵》残本与《唐韵》展开例证
从七世纪长安话与《切韵》音韵的对比
| 长安话 | 《切韵》音韵 | |
| 坚 | kji | Kji,记见开三之去 居吏切记志也说文疏也居吏切一。 |
| 鸡 | kiei | Kiei,鸡见开四齐平古奚切说文曰知时畜也易曰巽为鸡古奚切十鸡见开四齐平古奚切籀文。 |
| 金 | ,金见开三侵平居吟切金宝说文曰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薶不生衣百炼不轻从革不违西方之行生于土亦州名周为附庸国魏于安康县置东梁州后周改金州又金鼓释名曰金禁也为进退之禁也又姓古天子金天氏之后也又汉复姓有金留氏出姓苑居吟切九。 | |
| 共 | kjiuŋ | Kjiuŋ,共见三钟平九容切共城县在卫州又渠用切;共羣三钟去 渠用切同也皆也渠用切一。 |
| 姜 | kjiaŋ | Kjiaŋ,姜見開三陽平居良切姓也出天水齊姓本自炎帝居於姜水因爲氏漢初以豪族徙關中遂居天水也薑見開三陽平居良切菜名說文云御濕之菜史記云千畦薑韭與千戶侯等居良切十五。 |
| 强 | gjiaŋ | gjiaŋ,,强羣开三阳平 巨良切健也暴也说文曰蚚也又姓后汉有强华奉赤伏符巨良切四 强羣开三阳平巨良切 与强通用说文曰弓有力也;强羣开三阳上 其两切说文云弓有力也或作强又姓前秦录有将军强求又其良切。 |
2.3 以敦煌汉藏语言对比展开例证
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们利用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成绩卓著。目前已经刊布研究的汉藏对音材料,由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时的5种增至20多种。在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汉藏对音材料都不失为重要的参考资据。[3]
而这些专家学者们依据敦煌的汉藏对音材料所研究出来的语音资料,也为佐证唐朝官话提供了绝佳的例证材料。关于通过汉藏语言对比研究,为唐朝官话--长安话的试论这部分,我们引用罗常培先生、高田时雄先生和邵荣芬女士的研究,以辅佐例证。在罗先生的研究当中,罗先生发现前四种汉藏对音材料里,“模母除唇音字外还没有变u,鱼韵也游移于i、u 之间并没同虞韵完全混淆。不过鱼韵在《阿弥陀经》、《金刚经》里i多于u,在《千字文》里i与u不相上下,在《大乘中宗见解》里却 u 多于 i:由这两音的消长上看,恐怕从五代起,鱼、虞渐有混而不分的趋势了。在现代西北方音里,模韵已全变[u],鱼、虞两韵也已合而为[y],不过因为受声母的影响各方面却微有参差”。 [4]
而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先生则将模韵的情况进一步作了细分,“唇音字全部用-u 来写”,《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道安法师念佛赞》、《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也用-u来写,其余的用-o。鱼韵和虞韵的情况区别得很清楚,鱼韵用-i(-yi)、-u(-yu)两种标记法,而虞韵大多用-u。 [5]而且罗先生认为鱼韵字读-i 或 -u 找不出分化条件,这个观点高田先生也赞同。邵荣芬先生所写敦煌俗文学的别字异文中,鱼、虞两韵有一部分字相混,同时,鱼韵与止摄开口字相通,虞韵与止摄合口字。 邵氏的解释是“鱼一部分字 读-i,一部分字读-u,找不到条件,说明对音不一定可靠”。 [6] 另外,美国语言学家米勒也关注了罗先生书中提到的汉语效、 流摄字和韵尾元音-i、-u 的藏文转写,论述了汉藏对音材料中书面藏语 -u 和中古汉语-i的对应关系、语素d[a]、藏文的小词尾 Cu(即“辅音+u”)、汉语 ü 的藏文转写等问题。 [7]
在中古汉语的长安方言当中,在分析模、鱼、虞三韵时,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在圆唇元音无论是不带辅音韵尾(鱼模虞韵)还是带辅音韵尾(东冬钟韵),都表现出一种反常的面貌。日译汉音根据东韵字带不带i介音而给了这些字以不同的元音,并且也给了同用的东钟韵以同样的元音,越南译音将其分为两类,把其中的钟韵(全是三等字)混同于东韵三等。再有,日译汉音和越南译音给了冬韵(全是一等字)和东韵一等以相同的元音,这个元音与三等的元音不同。通摄的混用可以在司马光那里得到证实,司马光把冬韵和东韵一等合为一图,把钟韵和东韵三等合为另一图。因此,东韵和同用的冬钟二韵并没有形成元音不同的两个韵摄,而是一方面出现了部分字的混同,另--方面又在内部分而为二。
不过只需提醒一下,我们用来构拟中古汉语的文献资料彼此间在时间上并不一致,再需指出这些区别全都是同样的道理,并且比较晚近的文献还能证明区别的范围扩大了,这就足以使人承认其中的矛盾只不过是由语言的演化所造成的。鱼模虞三韵中的怪现象也是同样的缘故。[8]
因此,从敦煌对音表和长安方言当中模、鱼、虞三音同时发生的混淆现象中来看,不难以得出一个导向唐王朝的官话是长安方言,或者说是长安话这么一个结论。 总结
从中古汉语音系《切韵》一书的对照看,本文通过7世纪的长安话与《切韵》一书,以“坚”、“鸡”、“金”、“共”、“姜”、“强”六个字的发音举例、对比,以此例证从中古汉语音系的角度,得出唐王朝的官话就是长安话。
同时,利用中外学者们通过敦煌汉藏对音材料关于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得出的卓著成果,以鱼模虞韵为切入点,同比对长安方言进行比对,发现无论是敦煌汉藏材料当中所表现的唐代语音,还是《唐代长安方言考》当中的长安方言,都有一个奇妙的语言现象,即鱼模虞韵的一个混同。也因此,我们通过基本演绎的推论,得出长安话就是唐代的官话这一结论。
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和例证,本文因此提出一个结论,即中古汉语当中的长安话就是作为唐王朝都城的市民、中上层阶级的精英和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语言工具,或者说是官话。
参考文献:
【1】[论文集]水华.唐代长安、洛阳诗歌音韵研究[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08):13-14.
【2】[论文集]史淑琴.敦煌汉藏对音材料研究概述[J].丝绸之路,2012(24):14-18.
【3】[连续出版物] 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M].台湾: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
【4】[论文集]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第 153 页.
【5】[论文集]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第116~119页.
【6】[论文集] 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年 第 3 期,第 210 页 ,第 204~205 页.
【7】[论文集] 米勒(R. A .Miller)著、史 淑 琴译:《关于敦煌汉藏对音的几个问题》 , 《西北方言与文化研究集刊》, 华东师大出 版 社 2012 年版。 原题为“Some Problem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s of Chinese from Tun-Huang”,载《华裔学志 (Monumenta Serica )》第 26 期,1967 年,第 123~148 页.
【8】[专著].《唐代长安方言考》[F].[法]马伯乐著:聂鸿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 75 页.